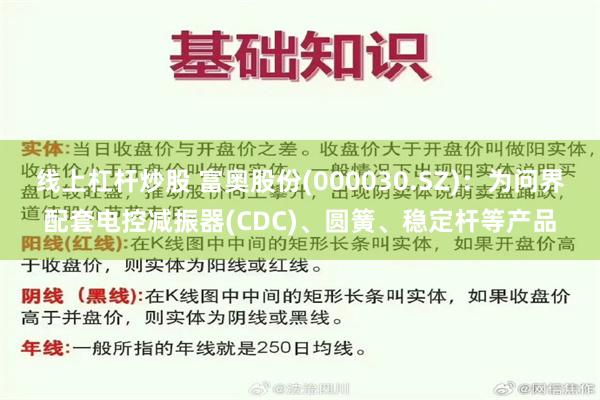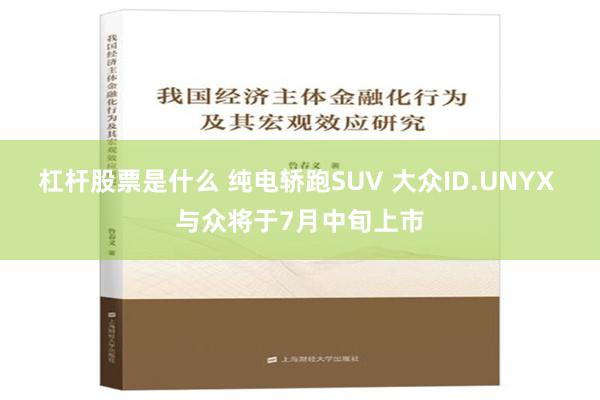“我家有一个大园子,这园子里蜂子、蝴蝶、蜻蜓、蚂蚱,样样都有。蝴蝶有白蝴蝶、黄蝴蝶。这种蝴蝶极小,不太好看。好看的是大红蝴蝶,满身带着金粉。蜻蜓是金的,蚂蚱是绿的。蜜蜂则嗡嗡地飞着,满身绒毛,落到一朵花上,胖圆圆的就跟一个小毛球似的不动了。祖父一天都在院子里边,我也跟着他在里面转。祖父戴一顶大草帽,我戴一顶小草帽。祖父栽花,我就栽花;祖父拔草,我就拔草。祖父种小白菜的时候,我就在后边,用脚把那下了种的土窝一个个地溜平。其实,不过是东一脚西一脚地瞎闹。有时不单没有盖上菜种,反而把它踢飞了。祖父铲地,我也铲地。因为我太小,拿不动锄头杆,祖父就把锄头杆拔下来,让我单拿着那个锄头的“头”来铲。其实哪里是铲,不过是伏在地上,用锄头乱钩一阵。”
《祖父的园子》里,萧红这段对童年的描写瞬间引起了我情感上的共鸣。那个戴着小草帽跟在祖父身后在园子里瞎捣鼓的小女孩,不就是小时候的我吗?童年最初的记忆,鲁西南农村姥姥家,有房顶上淘气的小花猫,有院子里憨态可掬的小黄狗,有挂在屋檐下一串串金黄的玉米,有伸长了脖子追着我跑的大白鹅,还有瓜果蔬菜恣意生长、蜜蜂蝴蝶随风飞舞的院子。
特斯拉此前已于6月中旬将其总部从特拉华州迁至得州。
勤快的姥姥喜欢在小院里捣鼓她的花花草草菜菜,与其说是院子不如说那是姥姥的小菜花园,东南西北各个角落都被她充分利用上了。一棵大榆树立在西北墙角,榆树下不远处的空地也被姥姥栽上了小青菜, 东面一大块地都被种上了花生,南面则靠墙种摆满了盆盆罐罐。有时候,我也陪姥姥一起在院子里瞎捣鼓,姥姥摘菜,我把菜拽出来喂小鸡;姥姥刨花生,我在花生地里乱踩一通;姥姥给花施肥,我拉着盛满了牛粪的小筐满院子乱跑……
我喜欢跟着姥爷去村头打水,他在前面挑着扁担走,我在后面拽着一摇一晃的小空桶,连跑带跳地跟着他。姥爷打水的时候,我就在一旁安静地玩小石子。等到姥爷挑好水踮着脚吃力地往家走时,我紧随其后,边走边踩木桶里溅出来的水花。姥爷在前面累得哼哼哧哧,我在后面乐得嘻嘻哈哈。
有一回,我们又去挑水,不知谁家的大花公鸡偷偷溜了出来。大槐树下,它大摇大摆地走来走去,一副气定神闲又威武十足的样子。姥爷照例打他的水,我依旧专心玩小石子。忽然,大公鸡竖着大红冠子,伸着大粗脖子,瞪着大眼珠子就朝我奔来。说时迟那时快,就在大公鸡要叨住我的屁股时,姥爷一把抓起地上的扁担,气势汹汹地朝那只鸡戳去。大公鸡一看情形不对,立马撅着大屁股掉头就逃。原本被吓哭的我破涕为笑,那一刻,姥爷就是我的守护神。
童年、故乡、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深深地影响了一个人的一生。很庆幸,在人生最初的五年里,姥姥和姥爷给了我无限的包容和无尽的宠爱。那段岁月虽然短暂,却成了日后最美好的回忆。他们照亮了我的童年,也照亮了我的创作之路。我从童年走来,又朝故乡走去,在记忆的滤镜下,儿时的故乡笼罩在淡淡的金光中,闪闪的亮亮的。我把对他们的思念和对童年的怀念收集在《金色童年》里,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,没有天马行空的想象,但却有最真挚的情感和最朴素的快乐。
回忆童年一旦开了头便一发不可收拾,有段日子,只要看到跟童年有关的绘本,我便拔不动腿了。我收集了满满一箩筐的“童年”,仿佛拥有了它们就拥有了穿越回童年的魔力。《祖父的园子》里,有恣意飞舞的花蝴蝶,挂满枝头的脆黄瓜,绿油油的小白菜,毛嘟嘟的狗尾巴草,飒飒作响闪闪发光的榆树叶子,乖巧可爱又黏人的小猫,还有慈祥和蔼的祖父和天真烂漫的小孙女……萧红的文字和田菾的插画都有着孩童般的天真与真诚,只是轻轻拿起这本书慢慢翻看每一页,便有重温童年的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我们乡村的小孩,记忆里都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。正如田菾在《致我们亲爱的故乡》里描绘的那样:“儿时的岁月有快乐也有忧伤,那深沉的感情就如当年灰暗潮湿又温暖的房间,件件物什都如一本小说,一部电影,讲述着我们的生活和回不去的时光。” 时光一去不复返,美好的记忆却能在画笔下重现。会画画真幸福呀,在田菾神奇的画笔下:那挂满枝头的红柿子,彩虹斑斓的呼啦圈,毛茸茸的小鸡小鸭,挂在耳朵上的番薯秆子,披在身上的花床单,屋檐下的大水缸,外婆手里的旧蒲扇,乡间小路旁的稻草人,村里那片芦苇荡,还有屋顶缓缓升起的炊烟和阳光下的老木屋…… 那些熟悉又亲切的场景瞬间把我们拉回了属于她,也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童年。我把田菾的绘本分享给好朋友,她边看边感慨:“呀,这不就是我小时候嘛!”
《祖父的园子》
萧红 著 田菾 绘
《致我们亲爱的故乡》
作者田菾
《那山 那人 那狗》
彭见明 著 田菾 绘
稿件初审:骆玉龙
稿件复审:董彦乐
稿件终审:刘 燏长春股票配资